白岩松:我认为,公平对每一代年轻人都重要,对今天的年轻人同样重要。每一代的公平都有不同内涵,对于今天非常困难的年轻人而言,他们不一定想要很大优待,但公平是个大前提,这是我当初走上就业岗位时非常感恩的收获。我希望今天的年轻人能够获得与公平相关的一切环境。
不管是曾经在政协履职,还是自己的新闻本职,你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眼前,而是如何让中国的明天更好,支撑你走下去的背后一定是公平和进步。因此建议一定要具有前瞻性,即使当时不被理解,但随着时间推移形成的共识会更多。
谈内卷与躺平,今天年轻人是弱势群体,需政策撬动起积极性
记者:近年经常能从年轻人嘴上听到“内卷”与“躺平”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,如何看待这种状态?当理想照进现实,年轻人如何做好平衡?
白岩松:十几年前我就在关注这个问题。这几年越来越强烈感受到年轻人心中有怨气的原因是,他们现在是社会的弱势群体,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人。当年我们青春的时候,我们是社会的强势群体,出生于60年代,受教育在80年代,80年代的我们兜里什么都没有,但我们有明天。《明天会更好》这首歌就是40年前写的,它成为我们这代人内心最丰富的东西。当时各个年龄层达成共识,年轻人是社会关注的重点,当年年轻人四处受宠,机会无数,破格提拔机会很多,不能不说,这的确是时代红利。
记者:为什么说今天的年轻人是弱势群体?
白岩松:有以下几个标志:首先,现在年轻人虽然学历很高,但是在家里的地位并不高,他们收入大比例没有父母高,并非家庭命运的改变者。我们经常听到老人教训年轻人不愁吃不愁喝,但每天垂头丧气,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就感。我们这一代人虽然一开始什么都没有,但在逐渐拥有的过程中,带动整个家庭发生改变,获得了成就感。
其次,目前年轻人机会成本大量下降,年轻人越来越认为,努力不一定有回报。因此“躺平”“内卷”等情况变得更加严重。随着机会成本减少,人数增多,人们自然会去“卷”。因此,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声音背后的因素。
第三,这代年轻人渴望爱,然而却又“无力爱”。各种现实障碍和因素导致他们结婚越来越晚,甚至谈恋爱都很难,我之所以说他们渴望爱,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养猫养狗比我们那时候多,猫和狗都成为了自己的孩子。
以上三种因素相互纠缠,决定现在年轻一代是弱势群体。最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上无力感很强,不像80年代的年轻人什么都没有,却被整个社会捧到了“明天靠你”的位置。
从政策角度看,我们现在必须大力向年轻人倾斜,振作起时代的信心: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经济消费和民营经济,我们目前正在努力,另一方面的信心需要社会的年轻人开始相信明天,开始积极振作起来,这也需要政策的推动。
记者:如何通过政策提振年轻人的信心?
白岩松:我认为,要有很多针对性政策,首先要推动更充分的就业,这是第一民生,接下来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,成本不高,但我看中这样的政策示范、激励与信号的作用。在这10年到12年间,能不能让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个人所得税起征额由5000直接跳到12,000元。现在的年轻人需要打拼、租房、考虑生育,虽然现在生育比例在降低,这反而需要用政策来撬动他们。这样单位也愿意给你开更高的工资,因为单位可以不交税,或者把原本要交税的当成增加的工资部分。
另外,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工作不稳定,政府和企业能否给40岁以下尤其是35岁以下的灵活就业人员更多社会保障。现在很多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都是缺失的,这一代人60岁以后怎么办?他们可能没有考虑过,但社会需要考虑这些问题:当年轻人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和迷茫,甚至悲观的时候,他会选择婚姻吗?选择婚姻之后他会要孩子吗?当他对未来不确定,一天累得像牛马似的,他会认真吃一天三顿饭吗?他的健康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冲击?
当社会最年轻的一代对婚姻、孩子和自己的健康没有任何保障,社会信心的另一半来源于何处?我认为,要让年轻人不要担心60岁之后的事情,这样他们才能够成长。当企业能承担这些责任时,企业去承担。当他们没有工作时,政府需要承担责任,使每个中国劳动者,无论是终身雇佣人员还是灵活就业人员,在60岁后有清晰的社会保障,他们才敢对未来有预期,仅靠口号和画饼没有用,陪伴才有用。
从政府角度来看,出台有明确信号和有用的政策才是有用的,让年轻人明确知道,即使没工作只能靠低保生活,但他们明白60岁后依然可以有社会保障,他们才可以用一生的长度考虑家庭、婚姻、孩子和健康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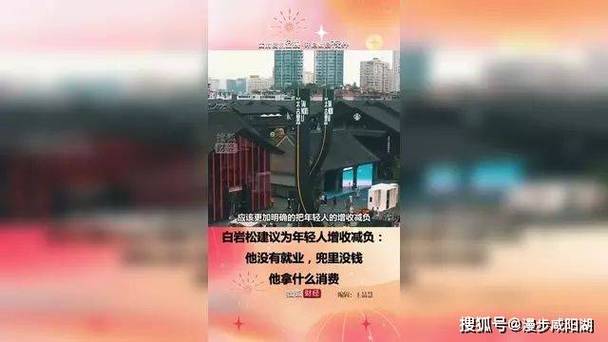
提振整个社会的信心,要让年轻人再次成为受益者,从政策多方面进行调整,并需要这个政策持续10到12年。
记者:为什么不断强调对年轻人的政策延续性只需要10到12年?
白岩松:近年来,我们生育的最高峰拐点出现在2016年,之后开始直线下降,到了2022年跌到了1,000万以下,这两年一直在1,000万以下。因此10年到12年后年轻人的就业不再是问题,没有那么多劳动力供给了,所以不担心12年之后的年轻人在社会上的地位,我们需要这10到12年对年轻人有明确的政策扶持。
有很多人说这对于中老年人不公平,但这批年轻人是他们的孩子,帮助他们何尝不是在帮助今天的老人。我之所以反感“啃老”这个词,是因为如果社会把很多工作做好,他们就不会啃老,老年人也获得了解放,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养老过程中,也给孩子减轻负担。
谈“啃老”现象,社会要让年轻人有制度有保障可“啃”
记者:当前80后和90后已成“啃老”主力军,如何看待年轻人依赖家庭支持的社会现象,背后反映什么问题?
白岩松:从亲情角度来看,成为所谓的“职业子女”并不坏。从社会角度来看,这是不可以的,因为是社会的保障不够,将应该承担的保障交给父母,让年轻人背上“啃老”的骂名,这个词带有很强的贬义。因此,我认为这不公平,如果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失职,那么应该进行调整,让年轻人有制度可“啃”,有保障可“啃”,“啃老”这个词就会逐渐淡化,我不相信年轻人愿意啃老。其实,大家经常忽略一种心理问题,即使父母很乐意给他很多钱,10个孩子9个会不开心,他仍然愿意实现自我价值。
随着科技和社会环境的变化,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,变得更不开心和更不幸福。因为每天在庞大比较体系中,他们不再是心理强大的一代,抑郁、焦虑普遍附着于现在年轻人身上。在带这几届学生过程中,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成为一名心理老师,需要带领他们走出冰河,我经常用的词是“与自己和解”和“融化”,他们过去心中有块冰,希望被逐渐融化。经过这些经历,我已调整了原来的期望值,希望通过两年教育帮他们变成活力满满的人。
谈AI对媒体的冲击,优质答案取决于能否提出更高质量的问题
记者:面对近期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统岗位的冲击,您怎么看?今年有些地方开始有AI记者出现,我们如何不被替代?
白岩松:首先,一方面我们的传统媒体众多,全中国有差不多3000家电视台。但另一方面,优秀记者在减少,因为大家“种地”(内容生产)的数量越来越少,“种地”能力在减弱,所以我们更需要优秀的记者。从AI角度来看,新闻最重要的支撑在于“新”,这是学不到的知识,所以我从不担心这个问题。现在全民皆记者,全民皆摄影师。但是分母变大,专业摄影师更贵了,好的照片并没有增加太多。现在所有人都离不开传播,真正的事实是变多还是变少?谁来获得更有质量的事实?
现在的确是“一头多,另一头少”。媒体太多,做着相同的内容,能够种优质粮食的人开始减少,人类与机器相同,如果不训练,他们无法变得优秀。目前年轻记者的采访机会已经很少了,有人认为现在许多记者不会提问,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采访机会,所以我认为两手都要抓,两手都要解决。
我在带学生时告诉他们,提问比以前更重要了,因为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取决于你提出的问题。如果你的问题更有质量,更有针对性、更准确、更与众不同,它给出的答案就更好。
我们在做“学问”,但不问如何学。虽然今天谈论时非常现代化,但是老祖宗早在“学问”这两个字中就明白了道理,学和问是相互关联的。通过提问,我了解到他的水平如何,他好奇什么,他关注什么。这就是提问能力的重要性。同样的道理,在时代,优质的答案更取决于记者能否提出更有质量的问题,如果问题好,会给出好答案,现实中同样的人也会给出好答案。提问是记者唯一的武器,目前问题在于传统媒体在“种粮食”方面逐渐失去了机会,他们没有经过训练,我们无法期望他们能够进行有质量的提问。我认为传媒需要给年轻记者更多机会去接地气,去采访、提问、写自己的东西,而不是给他的东西。
面对海量信息,事实越是奢侈品。上世纪50年代,有记者采访罗素老先生提出两个问题,即对年轻人的忠告和对真理的看法,罗素的回答出乎意料,对于忠告只有一句话:“爱是明智的,恨是愚蠢的”。对于真理,他说只关注一件事,就是“事实是什么”,我非常喜欢这个回答。
